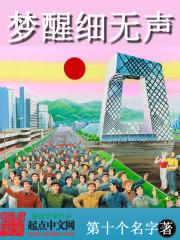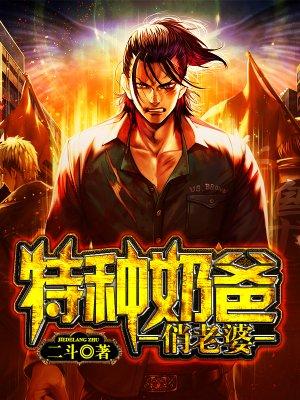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八章 心系故土福泽乡里(第3页)
闽商的慈善事业始于明朝。明崇祯元年(1628年),福建大旱,赤野千里,民不聊生,海商领袖郑芝龙毅然捐资,“招饥民数万,一人给银三两,三人给牛一头,用海舶载至台湾,令其芟舍开垦荒土。”不仅使人民免遭旱魔荼毒,更促进宝岛开发。清代迄始,福建慈善蔚然成风,善堂善会林立,如义仓、义塾、义渡此类的民间慈善机构多由闽商独力捐资设立,并受其管理。即使是官办色彩浓厚的育婴堂、普济堂,虽由官绅出资设立,但“商捐”却是其日常经费的重要来源,商人势力强大与否往往决定当地慈善机构规模。
翻阅史料,闽商“敦亲睦族”、“捐施贫乏”的记录随处可见,甚至还涌现了一批在全国颇具声望的慈善家。如晋江商人林瑞冈,早年曾参与上海“果育堂”创办,后又捐银五千两在家乡倡办“明善堂”,使“合镇贫乏家,孤寡有月资,病有医药,死亡有棺槽,行李困乏者助,济急扶危,遂以开一郡未有之善举。”除此之外,他还多次赈济灾民,名闻京师,被朝廷授予“乐善好施”匾额,并被赏戴花翎。
近代之后,由于地狭人多,许多福建人出海谋生,历尽艰辛,创业有成,成为侨商,他们虽有千万身家、却恋爱家乡、努力回馈桑梓,涌现了一批又一批可歌可泣的人物,像陈嘉庚、胡文虎等,使侨乡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即使在抗战的烽火岁月,许多闽商不惜毁家纾难,捐款捐物,救济难民,为抗战胜利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由此可见,今日闽商彪炳善界,是历史的传承与发扬。
《2010胡润闽商慈善榜》中也特别提及陈发树和曹德旺两位企业家在近两年都提出了将自己公司价值数十亿元的股份捐献给慈善事业的计划。2009年2月,曹德旺公开宣布将捐出自己所持福耀玻璃股票的60%——当时市值38亿元,成立以他父亲名字命名的“河仁慈善基金会”,以在中国范围内进行助学、救灾、救困、救急、宗教等慈善公益事业。8个月后的10月份,陈发树对外承诺捐赠当时价值83亿元的有价证券,有意效仿“盖茨基金会”的形式发起成立“新华都慈善基金会”。
计划成立慈善基金会的不仅有陈发树和曹德旺,2010年5月1日,正值恒安集团成立25周年之际,恒安向晋江慈善总会捐赠1亿元,设立“恒安慈善基金”;2009年10月,安踏体育发布公告称,公司董事局主席丁世忠及其家族成员以每股10港元的价格配售了8000万股安踏股份,约占安踏全部已发行股本的3。2%,共套现8亿港元,其中的部分资产将被丁世忠家族用于成立慈善基金会;2007年6月,中国龙工董事局主席李新炎成立了“李新炎慈善基金会”,基金会注册资金1000万元,注入资金3000万元重点开展扶贫助学项目。与此同时,还有闽商直接担任了慈善组织的领导,如恒安集团董事长许连捷、圣农集团董事长傅光明分别担任了晋江市慈善总会和南平市慈善总会的会长。
闽商之所以积极成立基金会,是出于把慈善公益事业做得更规范、更有效益的考虑。对此,福耀集团曹德旺的儿子——曹晖接受记者采访时,曾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现金捐赠好比吃面包,吃了就没有了,而成立基金会好像挖一口井,水能源源不断,才能更稳健、更持久地做慈善。”事实上,闽商的善举不仅在于回报乡里,远在他乡创业生活的闽商,也同样热心投入当地的慈善公益事业。以西南重镇云南为例,据云南省福建商会秘书长吴世界介绍,早在上世纪70年代起就有福建人跋山涉水到云南经商,经过30多年的发展,目前云南全省范围内经商生活的福建人近30万,投资总金额达千亿元。在云南,闽商和浙商、粤商是名列前三位的重要商帮,而在公益慈善捐赠榜上,闽商则是当之无愧的第一。据吴介绍,截至目前,云南省福建商会会员企业已经向云南当地慈善机构捐赠总计超过8亿元的善款,用于扶贫济困和帮助当地社会经济发展。
爱是人类共同语言,是成功的真谛,是人性的无私体现。正是因为大爱,闽商才能广受欢迎与信任,在千年岁月中屹立不倒,成为国际商界的璀璨之星。虽有极少数恶徒打着慈善旗号,招摇撞骗,但最终不为闽商群体所容,身败名裂,备受唾弃。在新的历史时期,闽商不仅能秉承大爱本性,竞仿先辈,更能推陈出新,成为时代弄潮儿。相信在未来,闽商还将继续扬帆善界,为和谐社会构建、海西建设发挥更大贡献,开创中国慈善新时代。
8.桃李满天下,发展教育事业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事业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历程,国家的发展壮大离不开教育,科教可以兴国。“凯旋归来”的福建商人更加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为了回馈桑梓,回报祖国,他们毅然的兴办起教育事业,孕育的英才遍及祖国大江南北。
办教育是一项无利可图的公益事业,而且,它不像捐建一所医院或者一座公园,一笔钱付出去,只要把房子盖成,也就大功告成了。办学不但需要一笔可观的创办经费,而且有关设备的添置、图书的购买、教员薪金的支付等等,是一项长期的沉重的负担。没有锲而不舍的毅力,没有强烈的爱国精神,是很难实现其抱负的。
创办教育,是陈嘉庚一生中的主要活动。他先后在厦门、集美、新加坡等地,捐资兴办了70多所学校,其中包括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有人估计,他一生用于办教育的经费,如果折合成今天的货币,约可达一亿美元。其中耗资最大,时间最长,影响最广的,首推他在其家乡创办的集美学村。
陈嘉庚在集美捐资办学,严格说来,早在1894年就开始了。当时他仅20岁,第一次从南洋回来,便把他所积蓄的2000元全部捐献出来,办起了“惕斋学塾”,这可称是他一生中最早的办学实践。但是,陈嘉庚在集美进行大规模的办学活动,则始于20世纪初。20世纪初的中国,贫穷落后,满目疮痍.国家饱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蹂躏,人民群众生活贫困,文化水平很低。那时,集美虽位于福建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同安县境内,但依然是民不聊生,文盲成堆。正如陈嘉庚在回乡时候所看到的那样,乡村十多岁的儿童,由于贫困失学,竟然成群结队,赤身裸体地嬉戏,令人叹息。整个集美村,甚至连一所正规的小学也没有。村中以封建宗族中的“房”为单位的各家族分别办了几所私塾,但教的都是《三字经》一类旧书。对此,陈嘉庚心中深感痛心,他认为:“那种情况,近则败坏风俗,远则贻误民族前途。”他着眼未来,为了提高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抱着“教育为立国之本,兴学乃国民天职”的爱国思想,决心捐资创办教育。
1913年1月27日,陈嘉庚经过周密的准备,正式开办了“乡立集美丙等小学校”,分设高等一级和初等四级。从此,在这个建村已有五六百年历史的集美.第一次出现了正规的学校。
为了加快家乡的教育建设步伐,陈嘉庚在集美开展办学活动的开始,就很注意抓好师资力量的培养,把它视为必须优先解决的大问题。1916年10月,陈嘉庚委托其胞弟陈敬贤回乡筹办师范和中学。陈敬贤先生不辞辛苦,四处奔走,精心筹划,于1918年3月10日正式开办了师范、中学两所学校,并将这一日期定为集美学校的校庆日。在这以后的近十年间,陈嘉庚利用其在南洋企业的赢利所得,先后创办了十多所学校,使原来文教事业极为落后的集美,迅速发展成体制完备的综合学村。在陈嘉庚先生的鼓励、资助下,闽南、闽西北和广东潮汕、梅州等地的许多贫苦学生纷纷前来求学。那时,集美成了华南一带有名的教育中心。
20世纪30年代初,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空前的经济危机,陈嘉庚在南洋的企业也因此受到很大的冲击。由于陈嘉庚多年来为创办教育花费了巨额资金,影响了其企业的自身建设,无法顶住世界经济危机的强大压力,1933年,他的企业被迫收盘,并于1934年全部停闭。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陈嘉庚先生所考虑的,仍然是集美、厦大两校如果关门停办,以后将很难恢复,这样一来,“影响社会之罪大”。所以他宁可使企业关闭,决不停办教育,真正实现他立下的“身家性命之利害得失,举不足撄吾念虑,独于兴学一事,不惜牺牲金钱,竭殚心力而为之”的誓言。
企业收盘后,为了坚持把集美学校办下去,陈嘉庚尽了最大的努力,他一方面自己节衣缩食,同时四方筹措,借助其亲友和集美校友的支持,继续向学校汇回—笔笔款项,保证集美学校各项教学活动的正常进行。在陈嘉庚先生的关注和支持下,集美学校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严峻考验。
为了提高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陈嘉庚一生不惜巨资,慷慨捐赠,义无反顾,相反地,他对于个人生活,却极为节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经常说:“应该花的钱,千万百万也不要吝惜,不应该用的钱,一分也不要浪费。”
陈嘉庚先生热心办学,不只是停留在捐款上。对于学校教育事业的发展,他也非常关心。在集美学校创办初期,为了聘请到合格教师,他抛下繁忙的商务,四处奔波,曾为此专程前往福州,也多次致函北京、上海等地,礼聘教师来集美任教,并请国内著名的教育家黄炎培先生代为招聘。据黄炎培先生回忆,仅1919年前后一年多里,陈嘉庚为讨论办学问题,就给黄写过30多封信。1918年集美师范和集美中学开办,陈嘉庚与陈敬贤—起,亲定“诚毅”两字作为校训,意在勉励学生们努力学习,百折不挠,奋发向上,忠诚报国。新中国成立以后,陈嘉庚先生从新加坡回到国内,他晚年长住集美,以七八十岁高龄,继续为集美学校的建设发展而日夜操劳。直到1961年6月,他因病重在北京住院期间,依然念念不忘集美校务,经常通过书信、电报、电话,询问和指导学校的工作,并立下遗嘱,将他所有的300多万元存款,除拿出100万元分别捐作北京华侨博物馆的建筑费和集美的福利基金外,其余全部交集美学校作为办学经费,连一分钱也没有留给自己的子孙。他还谆谆叮嘱后人,一定要把集美学校继续办下去。为了创建和发展集美学校,几十年来,陈嘉庚殚思竭力,矢志不移,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70年过去了,陈嘉庚先生的心血没有白流,这位爱国老人当年播下的一颗颗种子,已经结出了丰硕的果实。70年来,集美学校成绩突出,为国内外培养了一大批品学兼优的专门人才,其中仅中等以上学校的毕业生人数就达五万七千多人。他们中有许多人,已成为闻名中外的革命志士、专家学者、企业栋梁、艺苑名人,为祖国的解放、繁荣与富强,为人类的发展与进步,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如今,在这片“山明兮水秀”的南国胜地,6000多名学生,牢记着陈嘉庚先生生前的谆谆教诲,正在努力学习,在学海中吮吸着知识的乳汁。
9.集资“山庄”,凝聚乡情
山庄是粤商专门集资创设的安置客死异乡同伴灵柩的场所。广东商人长期在异地经商,有的长期寓居客地,直至老死他乡,这在当时繁华的大都市,因粤商人数众多,情况更为普遍。出于浓重的乡情意识,粤商集资创办了“山庄”,以使死者的灵魂得到慰藉。随着时间的推移,粤商山庄又成为所在地的一项重要的公益场所。
晚清以来,广州府和肇庆府商人在上海十分活跃,结成为广肇商帮。上海的广肇山庄坐落在新闸桥的西南方,最初由徐润的伯父徐钰亭等人捐资购买,占地30余亩,起初只是普通坟冢而已。清末旅居上海的广东人多达十七八万人。
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唐廷枢、徐润等又在上海添置土地八九十亩之多,扩大了山庄的规模,这次购买的土地靠近上海租界的繁华地段,建造有敦梓堂、地藏殿等设施,后又陆续购买土地,使得粤人山庄达到上百亩。
山庄本来只是对客死异乡者的临时安葬场所,但由于种种不确定因素,一些灵柩相当长时间后才能魂归故土,有的甚至永居客乡。活着的人总希望能通过某种仪式性的东西,让这些孤魂野鬼感受到他们的思念,又可借此凝聚同乡之情。
农历七月十五,是我国民间的一个重要节日。人们将佛教的盂兰盆节和道教的中元节合而为一,超度亡灵,普度众生,提倡孝顺与博爱。各地粤商多在这一天举行各种仪式悼念已故同伴,山庄成为重要的迎神赛会场所。上海的广肇山庄每年中元节都举行盛大的盂兰盆会,专门建立水陆道场,设坛讽经,届时各种纸扎的人物、供品,争奇斗巧,吸引了大批游人前来观赏。同时,在山庄的道场还会举办各种形式的杂耍、演戏活动,“游人毕集,极为热闹”。
广肇山庄举办的盂兰盆会已经超越了原先祭祀先贤的内涵,既带有摆阔式的广告味道,又具有宣传广东地域文化、丰富上海人精神生活的公益色彩。
广肇山庄在每年七八月间举办盂兰盆会活动时,上海地区非粤籍民众大约因迎神赛会有特色,或者以为粤商祭祀的神灵比较灵验,也纷纷涌来,美女香车云集,“吴娃楚艳亦莫不香车宝马络绎而来”,山庄周围,一时车水马龙,好不热闹。为了维持场内外的秩序,山庄主办者还聘请西捕(也就是租界警察局的西人警察)站岗放哨。
光绪年间上海竹枝词写道:旅申广肇有山庄,地步宽宏寄枢忙。每遇盂兰开会日,各般陈设独辉煌。广肇山庄竟被灵活的粤商开发为繁华都会的大聚会场所。
天津也是近代粤商活动的重要地区,清末张焘在《津门杂记》中记载,晚清以来,紫竹林梁家园一带的闽粤山庄,当地百姓俗称洋蛮坟地。民国《天津志略》记载,广东会馆于1916年在东局子半道之北购地200亩,划出20亩,新建山庄一所,山庄内遍栽花木果树,参仿西式。
天津的广东山庄和上海一样,也在每年七八月间,“醵资作会”,搭建起长达数百步的活动场所,悬挂着无数灯彩,聘请能工巧匠设计捆扎粤戏中的人物形象。在祭奠的那一天,锣鼓喧天,这些栩栩如生的纸人造型都挂在祭坛周围,“鼓动游人不下万计,车船轿马,流水游龙,倾城士女,空巷来观,熙熙攘攘”。至夜晚,彩灯齐放,“照如朗日”,还施放焰火,抛散食物,依然是香花鼓乐,游人兴致不减。
汉口的香山会馆每逢中元节,也举行隆重的盂兰盆会活动。据《申报》报道,1878年,有460多名粤商捐资数百金,举行祭祀神灵活动,讽诵藏经三昼三夜。1891年,粤商的祭拜活动也是讽经礼忏,铺张华丽。
山庄的建立,满足了旅居者叶落归根的愿望。山庄是乡情凝聚的表现,增进了同乡之间的感情,也是组建者赢得人心,提高威望的重要途径。
天龙邪尊
日更十章他是龙族龙子,却蜕变天赋失败,自巅峰跌落。圣女未婚妻自斩身孕,杀他证道。家族视他为耻辱,将他逐出,从族谱除名。绝境中,他苏醒前世记忆,华夏神龙...
问道章
穿越加重生,妥妥主角命?篆刻师之道,纳天地于方寸,制道纹于掌间!且看少年段玉重活一世,将会过出怎样的精彩?...
帝霸
千万年前,李七夜栽下一株翠竹。八百万年前,李七夜养了一条鲤鱼。五百万年前,李七夜收养一个小女孩。今天,李七夜一觉醒来,翠竹修练成神灵,鲤鱼化作金龙,小女孩成为九界女帝。这是一个养成的故事,一个不死的人族小子养成了妖神养成了仙兽养成了女帝的故事。...
梦醒细无声
重生潜入梦南宋不咳嗽完本作品,和本书人物也有相关,可以一起看。书友订阅群137118014由终点回到原点,洪涛又回到了他第一次重生前的时代,不过失...
少帅你老婆又跑了
少帅说我家夫人是乡下女子,不懂时髦,你们不要欺负她!那些被少帅夫人抢尽了风头的名媛贵妇们欲哭无泪到底谁欺负谁啊?少帅又说我家夫人娴静温柔,什么中医...
神兵奶爸
啥,老子堂堂的漠北兵王,居然要当奶爸?好吧,看在孩子他妈貌若天仙的份儿上,老子勉强答应了...